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人机与认知实验室”(ID: 9h_9c3c1f805cb8),作者满船空载月
《迷失的范式》书摘 (评论: 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
2018-12-03 转自 满船空载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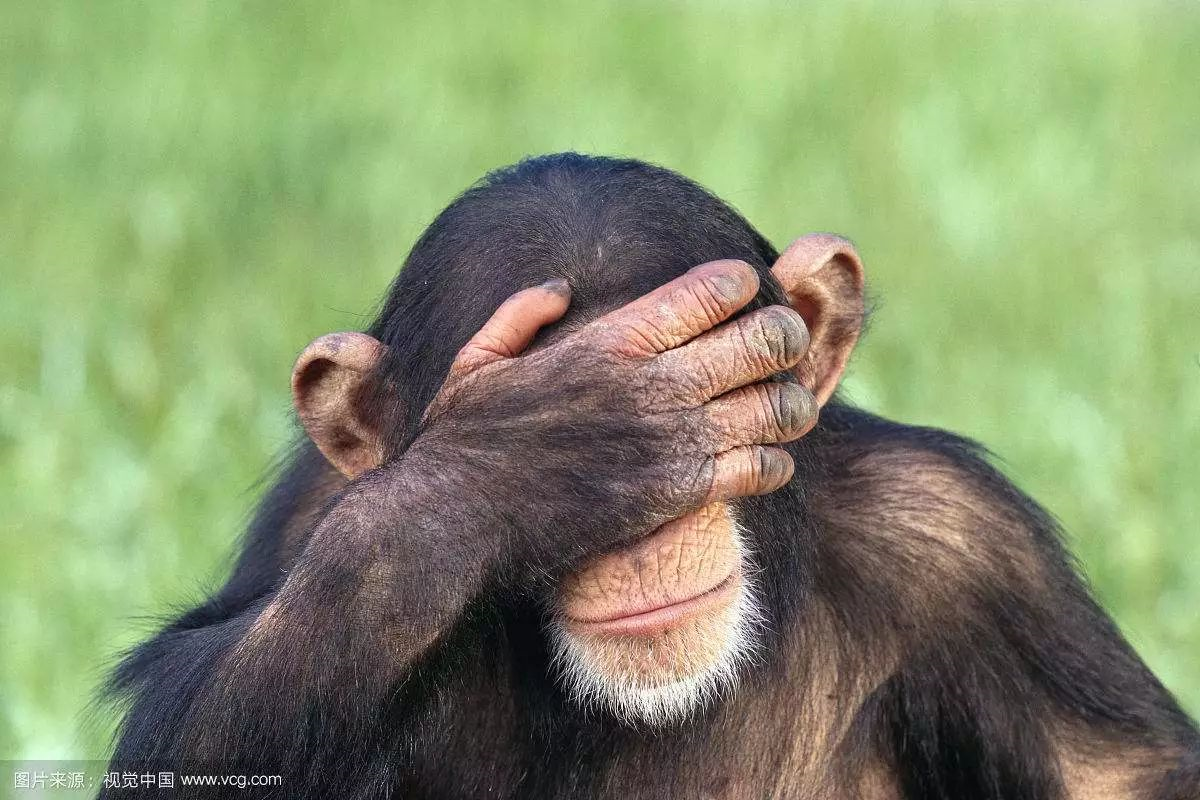
埃德加.莫兰说,本书是1971-1972年跨学科讨论会的产物,那次共同探讨的主题是“人的统一性”。之所以称为“统一性”,是因为传统的科学和思想“人”与“自然”分割开来,然后我们人类越来越变成了所谓的“工匠”和“智者”,离自然、离本源越来越远了。“人的统一性”则是重新将人类与自然结合在一起,重新看到人性不是一个脱离自然、与自然格格不入的实体,而是相融性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迷失的范式”的时代,推崇一种人占统治地位的范式、一种严格区分了人与动物的范式、一种刻意分割成了文化和自然的范式。传透这些范式的迷宫,带领我们重新去思考“人”和“人性”,即是本书的启示。
这就像市场和投资一样,充满了许多传统的、固有的认识范式,但实际上这些范式很多都是非常错误的,而大部分投资者的投资思想往往被这些错误范式占据了头脑。聪明和理性的投资者,非常迫切的需要从这些范式中走出来,重新去建立我们对市场和投资的认识,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成为成功的投资者,并且持续成功下去。
1、无序的力量,与组织本身的对抗性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总是存在着发生作用的无序的力量,它们不仅是个体具有的熵(衰老和死亡),而且是社会本身具有的熵。后者一方面来源于社会应该吸收掉的个体的随机性,另一方面来源于组织本身的对抗性,但是这种组织本身的对抗性在一定的范围内又是社会的复杂性所必需的。再说一遍,无序(随机的行为、竞争、冲突)的作用是含混不清的:它一方面是社会秩序的构成因素之一(多样性、变动性、灵活性、复杂性),但另一方面它又保持为无序,也就是说构成组织瓦解的威胁。不过进一步看,无序所维持的永恒的威胁给予了社会复杂的和生动的特点:永恒重组。与机械的有序根本不同,‘生动’的有序是不断再生的有序。而无序则不断地被组织所吸收,或者被回收而转变为其对立面(等级制),或者被排除到外部(异常分子)或被维持在外围地带。不断地被吸收、排除、抛弃、回收、转变,无序不断地再生而社会有序也随之不断再生。在这里展示了复杂性的逻辑、秘密、奥妙和自组织一词的深刻含义:一个社会因为它不断地自我破坏所以不断地自我产生。”(P29-30)
2、生物进化与文化发展的互相关联
“由于原人的社会文化的进步促进了大脑进化和青春化,而大脑进化和青春化又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复杂化,因此存在着一个选择性地互相关联的环路促进着族类、个人、文化、社会等所有层次上的复杂性的发展。
“……在青春化过程上的进步意味着被先天地编制好程序的刻板(本能的)行为的减少,对(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的极大开放,获得很大的可塑性和灵活性。大脑进化过程中的进步对应于脑神经元的连接可能性的扩展,新的组织结构或智能的建立;这种智能不仅是语言的,而且是逻辑的、启发性的和创造性的。文化发展上的进步对应着信息、知识和社会学识的大量增生,也对应着组织规则和行为模式的大量增生,而这意味着社会文化特有的程序化过程的发展。
“换言之,文化发挥着补充作用加入了本能(遗传的程序)衰退和组织性智能增进的过程,它同时被这个衰退(意味着青春化)和这个增进(意味着大脑进化)所增强,并为这两者所需要。它构成了一个‘记录器’、组织性的资本、信息的资泉,适于滋养大脑智能,给启发性的活动策略指示方向,给社会行为编制程序。
“由此展现了原人进化过程的生物-社会-文化的多方面交互关联。”(P72)
“这样,过去的把自然和文化对立起来的认识范式就崩溃了。生物进化和文化发展是原人进化这个总体现象互相关联、互相干预的两个方面、两极。从具有一定智力水平的灵长类动物和它们的已经相当复杂的社会开始,生物进化作为一个技术-社会-文化的多方面的形态生成过程而继续着,而这个过程又过来推动和刺激引起青春化和大脑发达化的生物进化过程。”(P75)
“向我们表明:心理学、社会文化、生物学的方面不能被看作是彼此隔绝或彼此等级性地重叠的。因此,在看起来相隔极其遥远和不能彼此化归的东西——比如最受遗传决定的性、高级神经活动以及介于中间的情感性(爱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和惊人的联系。
“……是智人脑的把多种成分联邦式地整合为一、加强其间的相互联系的结构,使得有可能把生物的方面、文化的方面和精神的方面(这些成分同时是互补的、竞争的和对抗的;它们的相隔程度依个人、文化、时代面十分不同)联邦式地整合在生物-心理-社会-文化的惟一系统中。
“……历史不是其他什么,只是无序和复杂化之间的互补、竞争和对抗的随机的联系。”(P115)

3、意识:超级复杂性结出的花朵
“我们已经看到,与大脑的超级复杂性连接起来的不仅有无序和错误的涌现,而且还有放纵、不稳定的冲动、超级的情感性,可能还有进入陶醉和亢奋状态(包括性亢奋)的能力。
“但是,如果在智人-狂徒的辩证法中看不到超级复杂性结出的花朵——意识,那将是很片面的。
“意识一向是照亮其他东西而自身处于阴影中的事物。它是个总体性的和难确定的东西。它不能与智人精神的高级能力和活动的整体分开。它可以说是这些不同能力和活动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干预的产物。它产生于它们的会合,并是这个会合本身。意识在神话和巫术大量滋生的地方飞跃发展,也就是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大张着的缺口中,在想象和现实彼此搭接的相互干预的边缘地带。意识的根源是承认这个缺口和这个交接地带,它产生于主体和客体、真理和谬误的双重的辨证相互作用之中。
“意识的现象同时是极端主观的又是极端客观的,因为一方面它在自身强烈地携带着个体我的感情存在,另一方面它又努力地客观考察不仅是外部环境(世界),而且是主观的我。换个方式来说,‘我’一方面把我作为主体又作为认识的客体来自我考察,另一方面在考察客观环境时使他特有的主体存在介入其中。
“意识这个现象以一种反思的能力为条件。这里使用‘反思’一词的双重化的含义,也就是说,通过这种能力,认识可以返观它自身,从而使自己变成认识的对象。只有在思想和概念自我客观化为词语和符号时这种能力才能出现,也就是说只在这时认识的系统才能够建立起来。这样,当一个认识系统遇到它不能解决的问题、困难、矛盾时,思维的主体就可能把他过去用以进行审查、研究和检验事物的系统变成审查、研究或检验的对象,甚而制订一个变成他的新的参考框架的元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揭示自己,随着它不断地把自己作为研究和分析的对象,它愈益感到自己像一个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卷入越来越复杂的真理和谬误的游戏中。”(P116-117)
4、缺乏复杂性的认识范式,如封闭的岛屿
“今天死去的不是人类的概念,而是人类的岛屿似的概念,这种概念把人类同自然和他的自然本性割裂开来;应该死去的是人类的自我偶像崇拜:他在自己理性制作的夸张的形象中进行自我欣赏。
“对一个局限于狭窄的心理-文化领域的人类学的丧钟敲响了,这个人类学有如飞毯漂浮在自然宇宙之上。对这样一个人类学的丧钟敲响了,这个人类学没有复杂性的意识,而它所处理的却是所有对象中最复杂的对象;它害怕与生物学有接触,生物学处理着不太复杂的对象但却建立在更为复杂的认识原则的基础上。
“对人类的一个封闭的、片段的和简化的理论的丧钟敲响了,而一个开放的、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理论时代开始了。
“基础人类学应该抛弃所有把人或者看作是超动物的(人类学圣经),或者称作是严格动物的(新的流行的生物学圣经)实体的所有定义;它应该承认人类是生物以便把他区别于其他生物,同时它应该超越自然和文化之间的本体论的非此即彼、二者择一的论题。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深入地考察这种双重作用而不仅仅是满足于跨骑在两个学科之间,如果我们想要真正获得一个开放的、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理论,我们就需要在复杂性的和自组织的逻辑来寻找其基础。”(P173)
5、传统真理,可能是复杂社会的致命错误
“人类的发展总是跟两类错误有关,一类是相对于再生信息的模糊性产生的错误,它可能导致朝向更高的复杂性的进化,另一类是导致失败和灾难的诱人上当的假象。今天,在可能使人类的第四次诞生变得可能的巨大危机中,错误和真理之间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被推至顶点。建立在约束的基础之上的低级复杂的社会的任何真理,对于建立在约束减少的基础上的超级复杂的社会来说可能是一种致命的错误。超级复杂的系统的任何真理对于低级复杂的系统来说也可能是错误。
“因此科学被引入意识的不确定性的游戏之中。意识,特别在危机阶段,紧张地摇摆于作为它的次要现象的本性和作为它的中心现象的本性之间,沉没于狂热之中或者相反地突然从狂热中解脱出来。此外还有其他的矛盾:意识今天好像是产生新的社会复杂性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而实际上社会复杂性是唯一能够创造意识的发展条件的。这说明意识取决于在政治中演出的游戏和政治所玩弄的游戏。但是在那里,科学-意识-政治相互作用和相互干预的辩证法也不是封闭的,因为它处于历史的解体-重组的巨大的辨证法的内部,后者作用于全球的所有社会和人类的总体。正是在这个更深广的辩证法中,自组织的创造性的游戏会产生更高级社会的新的局部组织、前所未有的形式、自发的雏形以及其他早熟的但具有预兆性的东西。因此,在集体才智无意识的社会形态发展与科学-意识-政治的辨证相互作用这两者的关联中,新的人类诞生将找到它的机会。
“这里必须非常认真地看待‘诞生’这个词,并因而推翻现代的观点:无论科学、意识还是社会都只看到‘成熟’的问题。其实科学并未处于它的最后发展阶段,它还有待重新开始。……一旦它从它的操纵着可怖的力量的方程式中走出来,它就结结巴巴,讲不清楚。我们还是处于认识的开端。同样地,如同我们已多次重复提到的,我们也处于意识的开端。最后,我们不是处于历史社会的一个可能的最高繁荣的时刻,而是处于一个真正的超级复杂的社会的前夜。”(P191-192)

